姚俊逸:关于我国商事调解的几点思考——从加强企业自主优先的角度分析
姚俊逸:关于我国商事调解的几点思考
——从加强企业自主优先的角度分析
二、正本溯源,让裁判者裁判调解员调解
在当事人无法自主解决争议时,争议解决的方式要么经裁判解决,包括诉讼、仲裁,要么经调解解决。尽管裁判与调解秉持一些相同理念,比如,要独立、公正、合法等,但在更大程度上,涉及两者的伦理规范、行为禁忌等泾渭分明,不可混用。
(一)自由的调解与不自由的调解。
调解应当在当事人意志完全自由的前提下进行。完全自由表现在当事人可以只根据其意愿决定调解是否开始、可随时结束,自主决定更换调解员,决定何时举行调解会议等,当事人做这些决定时不受干预、没有顾虑。裁判中的调解,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当事人的自主性不能充分发挥。
(二)有权力的调解员与无权力的调解员。
调解的成功取决于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员从中发挥引导、协助、促成作用。调解员没有权力就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评价,更无裁判权。非但如此,当事人还有权随时停止调解或更换调解员。调解员必须利用其威望、专业能力和高超技巧,维持调解程序的顺利推进;调解员要不断提高调解技巧,在调解中展现耐心,积极探寻共同利益,助力当事人达成协议。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商事调解的印象停留在观念落后、手段陈旧、“和稀泥”等方面。商事调解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充分体现其自身纠纷化解优势,扩大影响力,提升公众对其的了解度、认可度。
(三)裁判者调解应转变为裁判加调解。
笔者建议,裁判者调解应慎用,限定在少数特殊情形。通常情形下的纠纷审理,应转变为裁判加独立调解,也即在诉讼中或者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如有调解意愿或者法官、仲裁员认为有调解基础,应当委托给商事调解机构由调解员调解。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与部分法院、部分国内外仲裁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承担法院、仲裁机构委托的调解,已有成熟经验。让裁判者裁判,可以让裁判者专司裁判职责,不违背裁判正当程序与理念,提升裁判质量与效率;由调解员调解,可以开拓商事调解的服务范围,激励调解员提升调解能力水平,促进商事调解事业长足发展。
三、厘清边界,打通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最后一公里”
作为一项争议解决制度,调解结果即调解协议能否强制执行成为执行名义,或者是否有便捷路径启动强制执行,是调解争议解决机制完整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事人选择调解的重要考量因素。为支持商事调解发展,吸引商事主体运用调解,世界各国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支持调解协议的执行。一种是直接赋予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该公约规定经调解机构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可以直接在公约生效国家申请强制执行。另一种方式是不直接赋予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但只要经过法院认可(确认)即可获得强制执行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现状与问题。
笔者在《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编写过程开展的前期调研中发现,针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存在以下情形:
1.法院只对本院委托、委派的调解或者本案特邀调解员的调解协议给予司法确认,对其他来源的调解协议不予确认
2.法院对调解机构自主受理案件达成的调解协议,确认积极性不高,给予一定数量额度,不愿过多接收。
3.法院在司法确认时不仅审形式,而且审实体,要求举证材料多,周期长。
4.一些不予司法确认的裁定,存在法官说理不足、主观性强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当事人选择运用调解解纷积极性的打击是巨大的,严重降低了调解作为争议解决制度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有必要进一步检视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重构确认标准与方式。
(二)厘清法院裁判权与确认权。
在民商事领域,法院除了行使裁判权,还根据上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承担了司法确认职能。该司法确认与民商事纠纷的确认之诉不同,主要是对当事人签署的调解协议真实意思表示的确认。法院对裁判权与确认权的行使应该设定不同的标准尺度、程序时效、责任范围。如前述调研时发现的问题,不少法院依照裁判权的标准要求来对待确认权。这一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导致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难以实现以及调解协议可便捷得到执行的立法目的落空的问题。笔者认为,民商事领域的私法自治是我国和世界普遍接受的原则。在私法自治基础上,国家法律认可商事主体选择司法之外的私力救济——仲裁,确认仲裁的效力以及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力,体现了国家对于商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尊重和司法权的让渡。如果说商事仲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仲裁裁决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间接产物,那么商事调解更是体现当事人高度意思自治,调解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直接结果。国家司法机关采用相比仲裁裁决更为便捷、更直接的程序认可调解协议,会更合乎私法自治的逻辑。
(三)建立简便高效的确认机制。
如上所述,建议法院在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上朝着程序简单、效率更高的方向改进,侧重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对于是否会出现虚假调解、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调解协议被确认的问题,笔者认为,防范虚假调解并非司法确认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等均可在之后发挥防范作用。可以预见,如果法院能够简便高效给予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商事主体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够在很短时间内,甚至立等可取成为执行名义,商事调解的吸引力将可以得到极大提升,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涌向法院的情况也可以得到改善。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抓住商事调解发展机遇,推动商事调解蓬勃发展。展望未来,如果调解优先理念深入商事主体,如果调解组织优化制度提供更高质量的调解服务,如果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更有保障,商事调解的发展将会迎来新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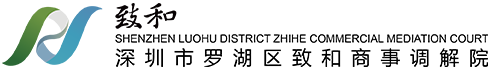


 400-133-5168
400-133-5168


